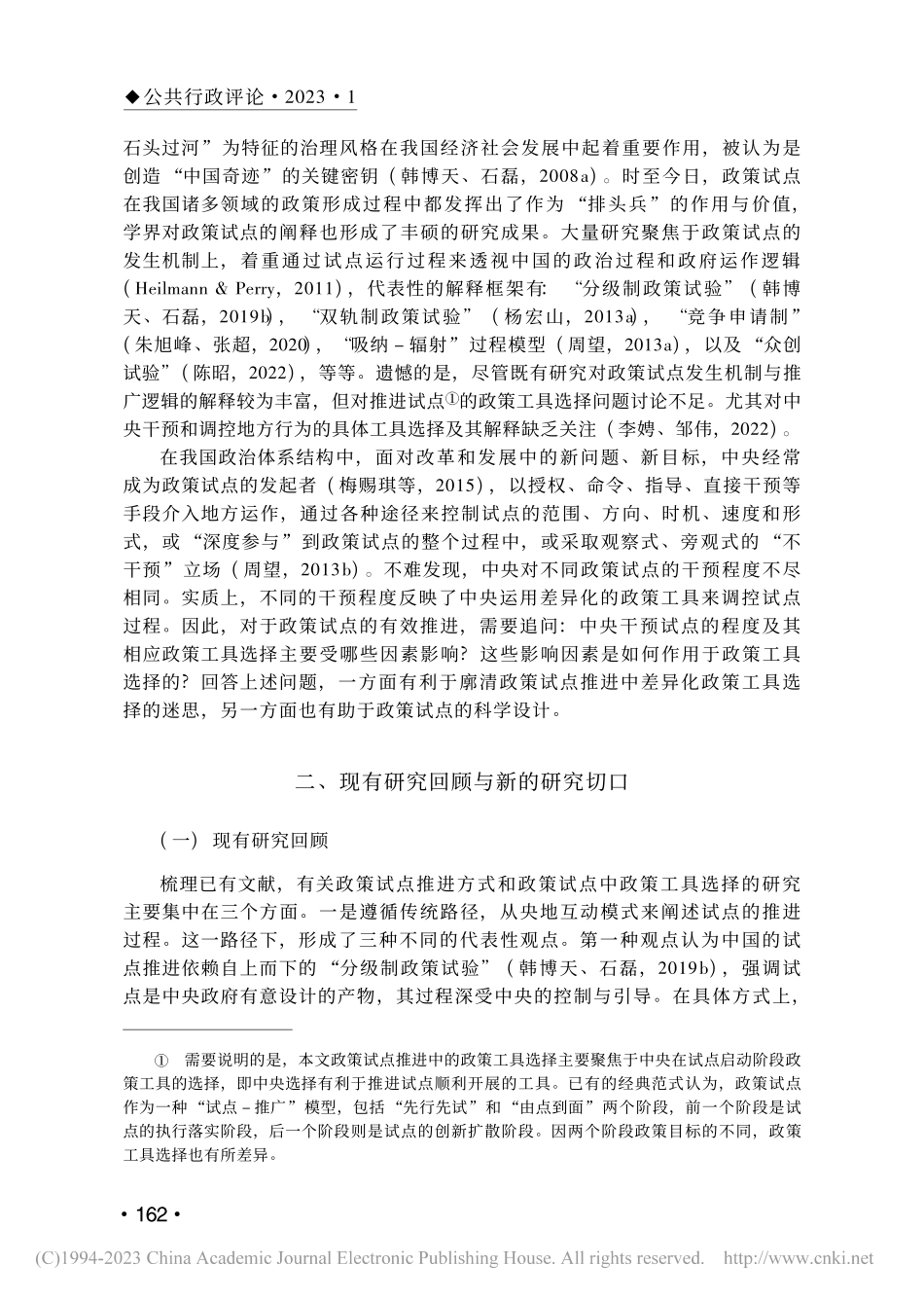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李强彬支广东李延伟*【摘要】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关键词】央地关系政策试点政策工具选择政策属性政策环境【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486(2023)01-0161-20一、问题的提出“政策试点”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标识性知识凝练与话语表达,这种以“摸着·161·*李强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支广东,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延伟,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曾在第三届“理解中国公共政策”工作坊宣读,感谢杨宏山老师、钱蕾老师和王建国老师的点评和有益建议。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主协商推进基层群众有效自治的长效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1AZZ005)。石头过河”为特征的治理风格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被认为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钥(韩博天、石磊,2008a)。时至今日,政策试点在我国诸多领域的政策形成过程中都发挥出了作为“排头兵”的作用与价值,学界对政策试点的阐释也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量研究聚焦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上,着重通过试点运行过程来透视中国的政治过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