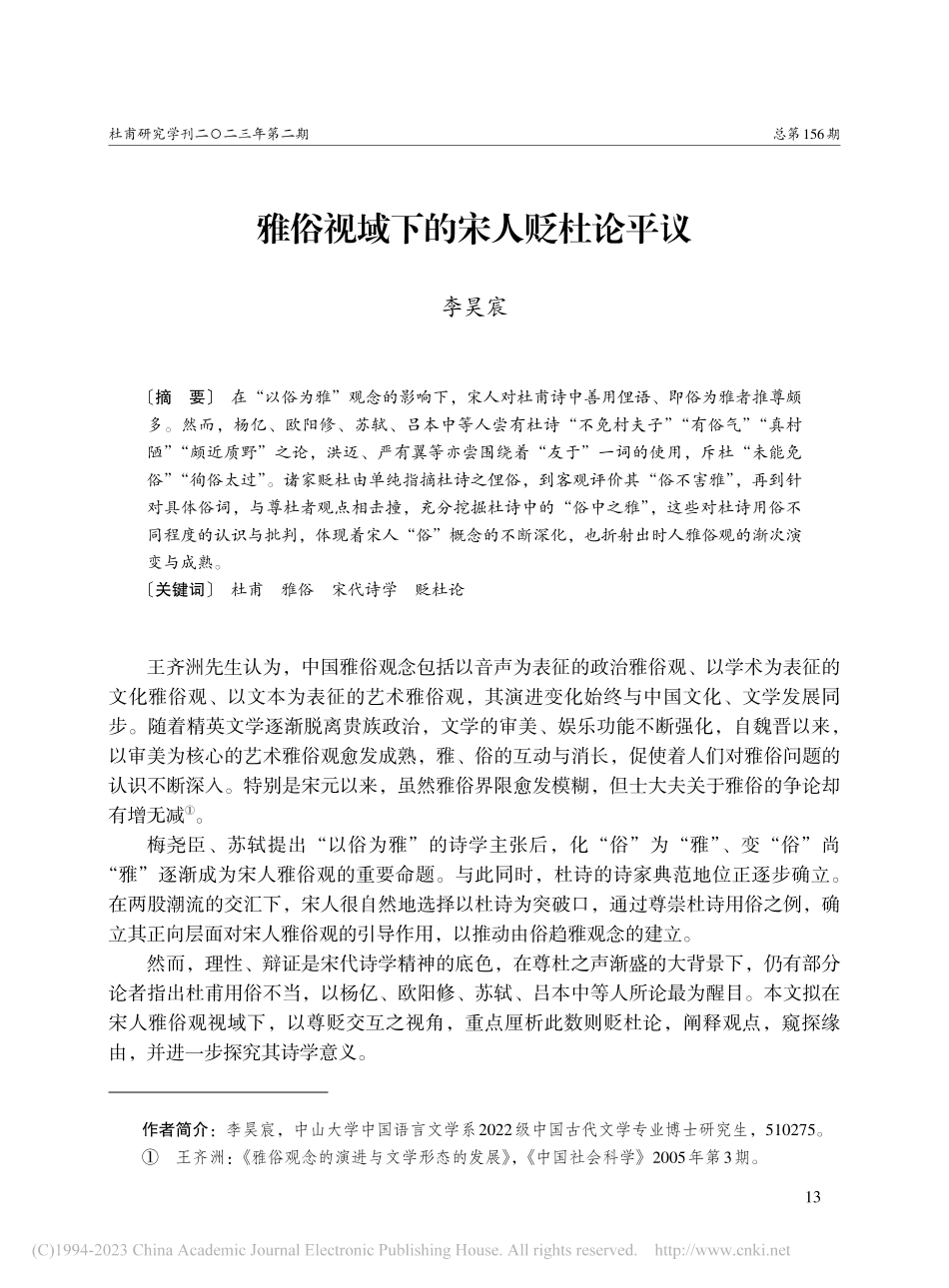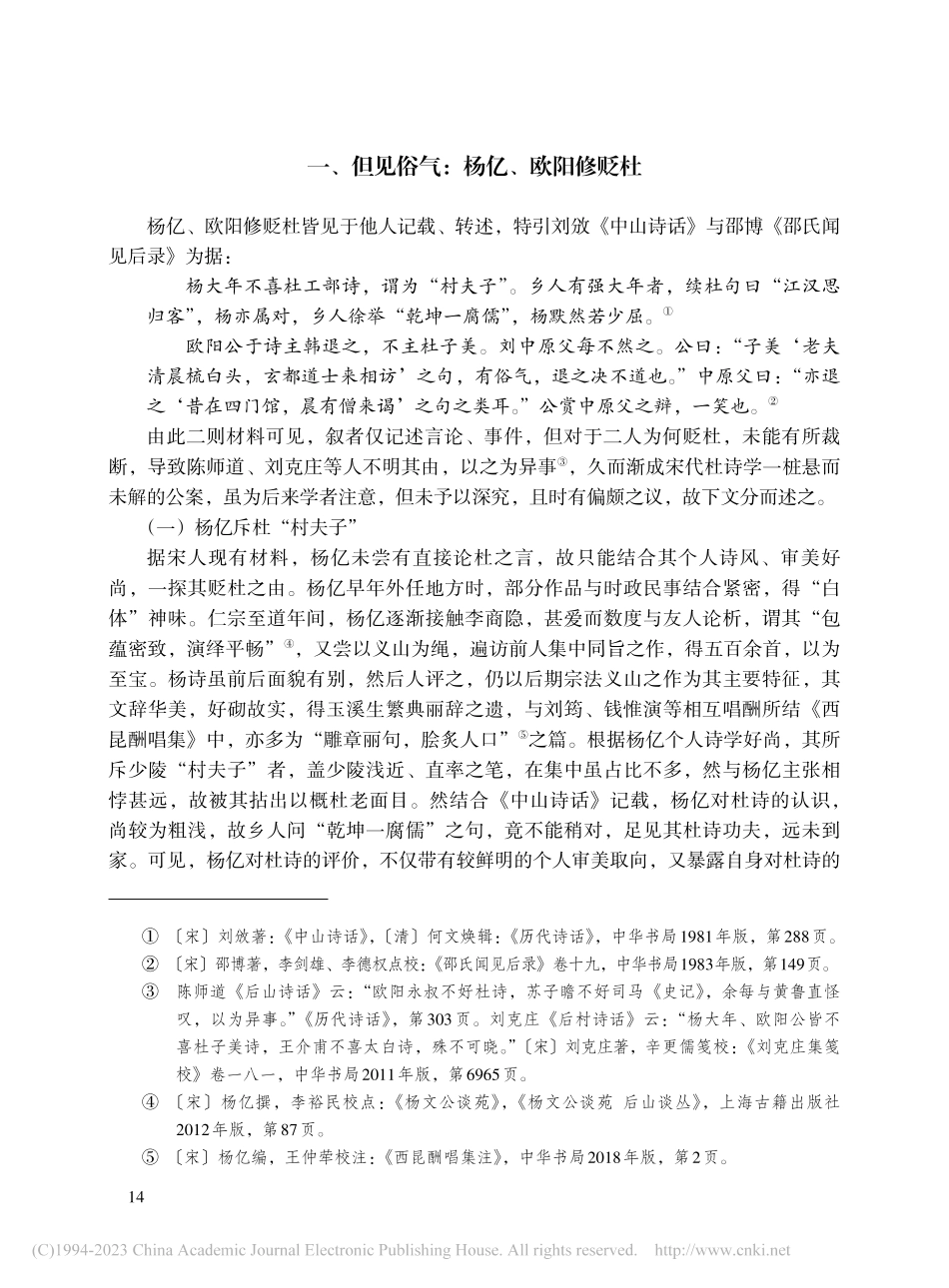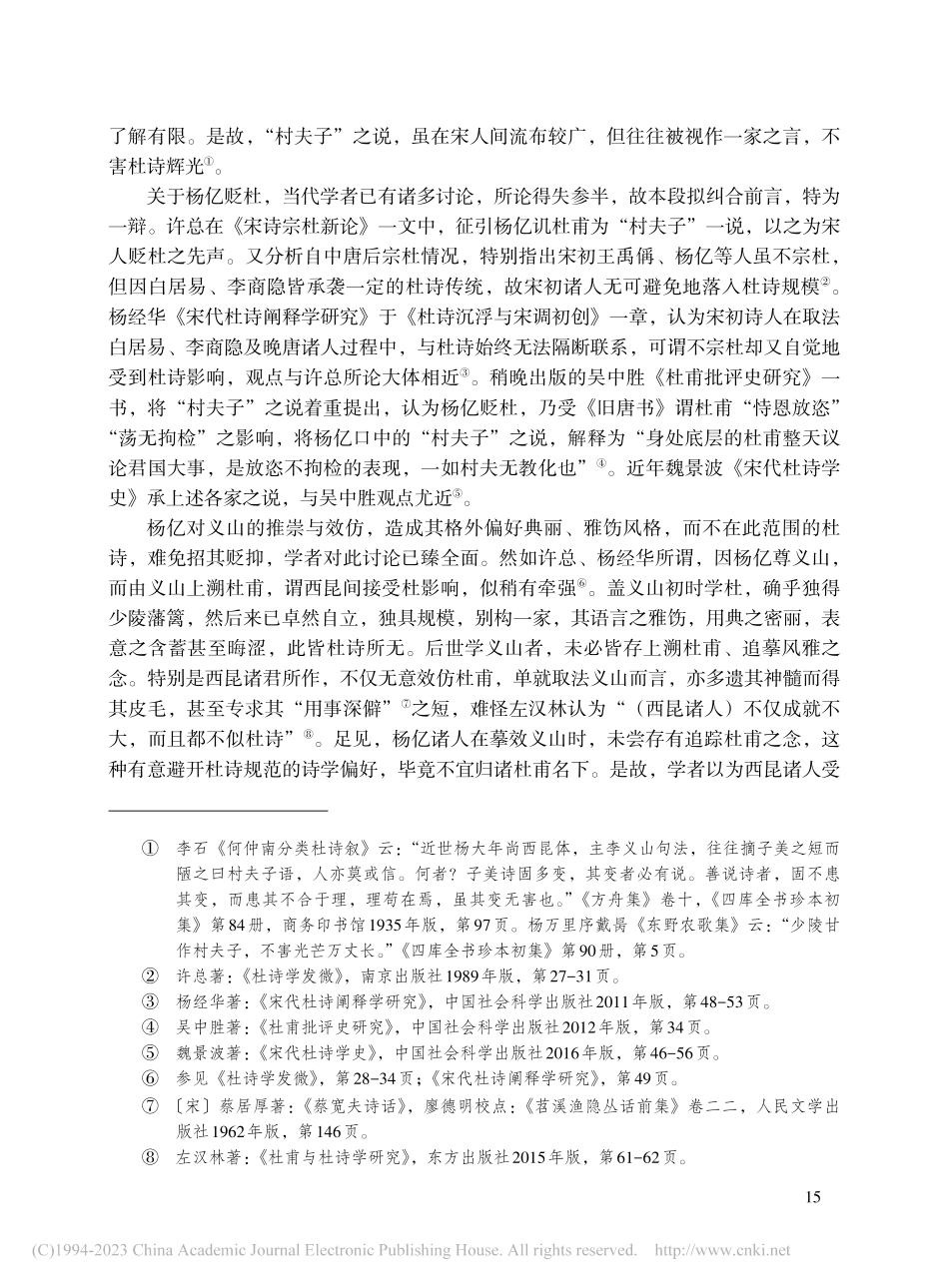杜甫研究学刊二〇二三年第二期总第156期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李昊宸〔摘要〕在“以俗为雅”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对杜甫诗中善用俚语、即俗为雅者推尊颇多。然而,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尝有杜诗“不免村夫子”“有俗气”“真村陋”“颇近质野”之论,洪迈、严有翼等亦尝围绕着“友于”一词的使用,斥杜“未能免俗”“徇俗太过”。诸家贬杜由单纯指摘杜诗之俚俗,到客观评价其“俗不害雅”,再到针对具体俗词,与尊杜者观点相击撞,充分挖掘杜诗中的“俗中之雅”,这些对杜诗用俗不同程度的认识与批判,体现着宋人“俗”概念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时人雅俗观的渐次演变与成熟。〔关键词〕杜甫雅俗宋代诗学贬杜论王齐洲先生认为,中国雅俗观念包括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其演进变化始终与中国文化、文学发展同步。随着精英文学逐渐脱离贵族政治,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不断强化,自魏晋以来,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愈发成熟,雅、俗的互动与消长,促使着人们对雅俗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特别是宋元以来,虽然雅俗界限愈发模糊,但士大夫关于雅俗的争论却有增无减①。梅尧臣、苏轼提出“以俗为雅”的诗学主张后,化“俗”为“雅”、变“俗”尚“雅”逐渐成为宋人雅俗观的重要命题。与此同时,杜诗的诗家典范地位正逐步确立。在两股潮流的交汇下,宋人很自然地选择以杜诗为突破口,通过尊崇杜诗用俗之例,确立其正向层面对宋人雅俗观的引导作用,以推动由俗趋雅观念的建立。然而,理性、辩证是宋代诗学精神的底色,在尊杜之声渐盛的大背景下,仍有部分论者指出杜甫用俗不当,以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所论最为醒目。本文拟在宋人雅俗观视域下,以尊贬交互之视角,重点厘析此数则贬杜论,阐释观点,窥探缘由,并进一步探究其诗学意义。作者简介:李昊宸,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510275。①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13一、但见俗气:杨亿、欧阳修贬杜杨亿、欧阳修贬杜皆见于他人记载、转述,特引刘攽《中山诗话》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为据: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若少屈。①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