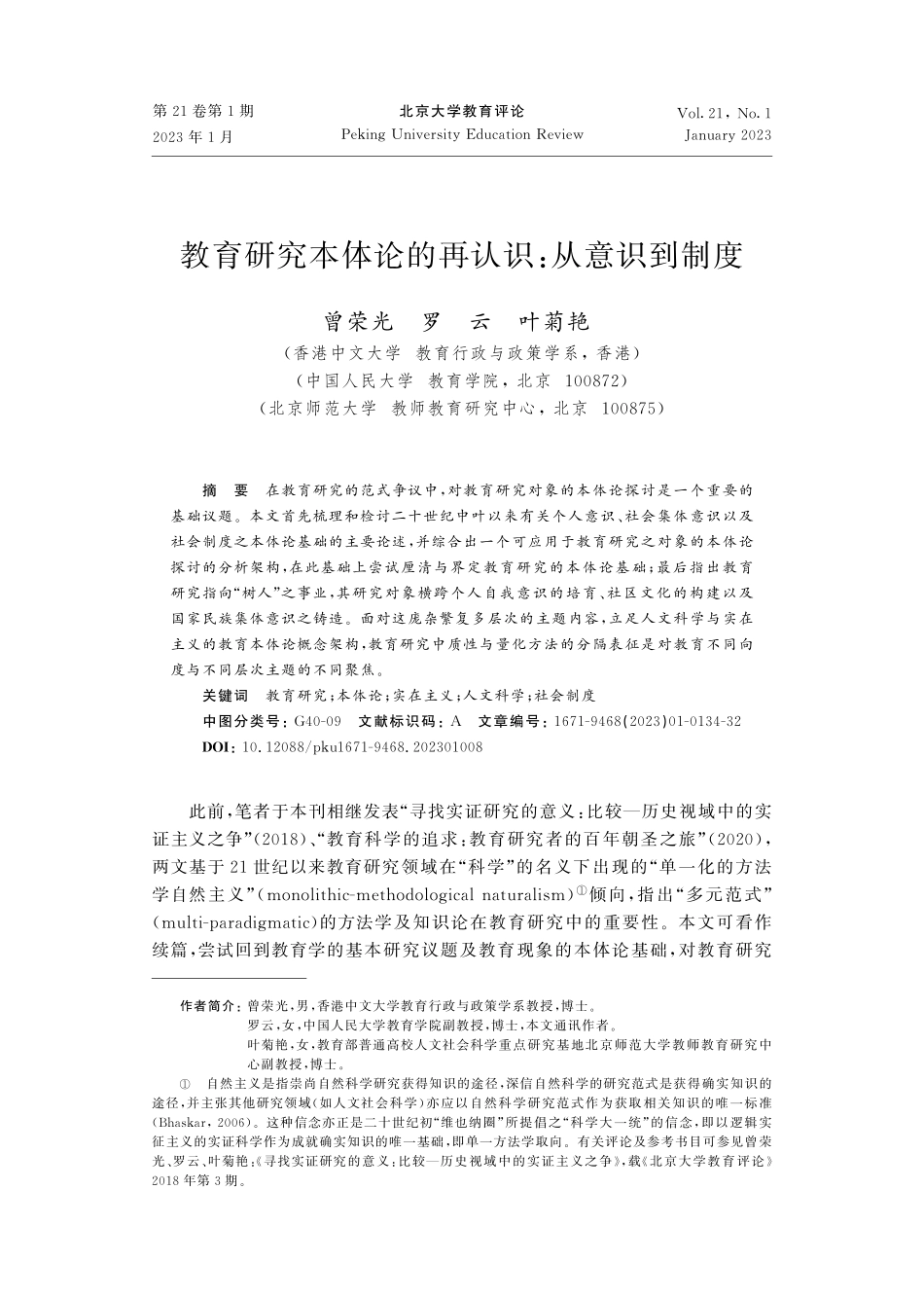第21卷第1期2023年1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PekingUniversityEducationReviewVol.21,No.1January2023教育研究本体论的再认识:从意识到制度曾荣光罗云叶菊艳①(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香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872)(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摘要在教育研究的范式争议中,对教育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探讨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议题。本文首先梳理和检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有关个人意识、社会集体意识以及社会制度之本体论基础的主要论述,并综合出一个可应用于教育研究之对象的本体论探讨的分析架构,在此基础上尝试厘清与界定教育研究的本体论基础;最后指出教育研究指向“树人”之事业,其研究对象横跨个人自我意识的培育、社区文化的构建以及国家民族集体意识之铸造。面对这庞杂繁复多层次的主题内容,立足人文科学与实在主义的教育本体论概念架构,教育研究中质性与量化方法的分隔表征是对教育不同向度与不同层次主题的不同聚焦。关键词教育研究;本体论;实在主义;人文科学;社会制度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23)01-0134-32DOI:10.12088/pku1671-9468.202301008此前,笔者于本刊相继发表“寻找实证研究的意义:比较—历史视域中的实证主义之争”(2018)、“教育科学的追求:教育研究者的百年朝圣之旅”(2020),两文基于21世纪以来教育研究领域在“科学”的名义下出现的“单一化的方法学自然主义”(monolithic-methodologicalnaturalism)①倾向,指出“多元范式”(multi-paradigmatic)的方法学及知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可看作续篇,尝试回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议题及教育现象的本体论基础,对教育研究①①作者简介:曾荣光,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博士。罗云,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本文通讯作者。叶菊艳,女,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自然主义是指崇尚自然科学研究获得知识的途径,深信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是获得确实知识的途径,并主张其他研究领域(如人文社会科学)亦应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作为获取相关知识的唯一标准(Bhaskar,2006)。这种信念亦正是二十世纪初“维也纳圈”所提倡之“科学大一统”的信念,即以逻辑实征主义的实证科学作为成就确实知识的唯一基础,即单一方法学取向。有关评论及参考书目可参见曾荣光、罗云、叶菊艳:《寻找实证研究的意义:比较—历史视域中的实证主义之争》,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