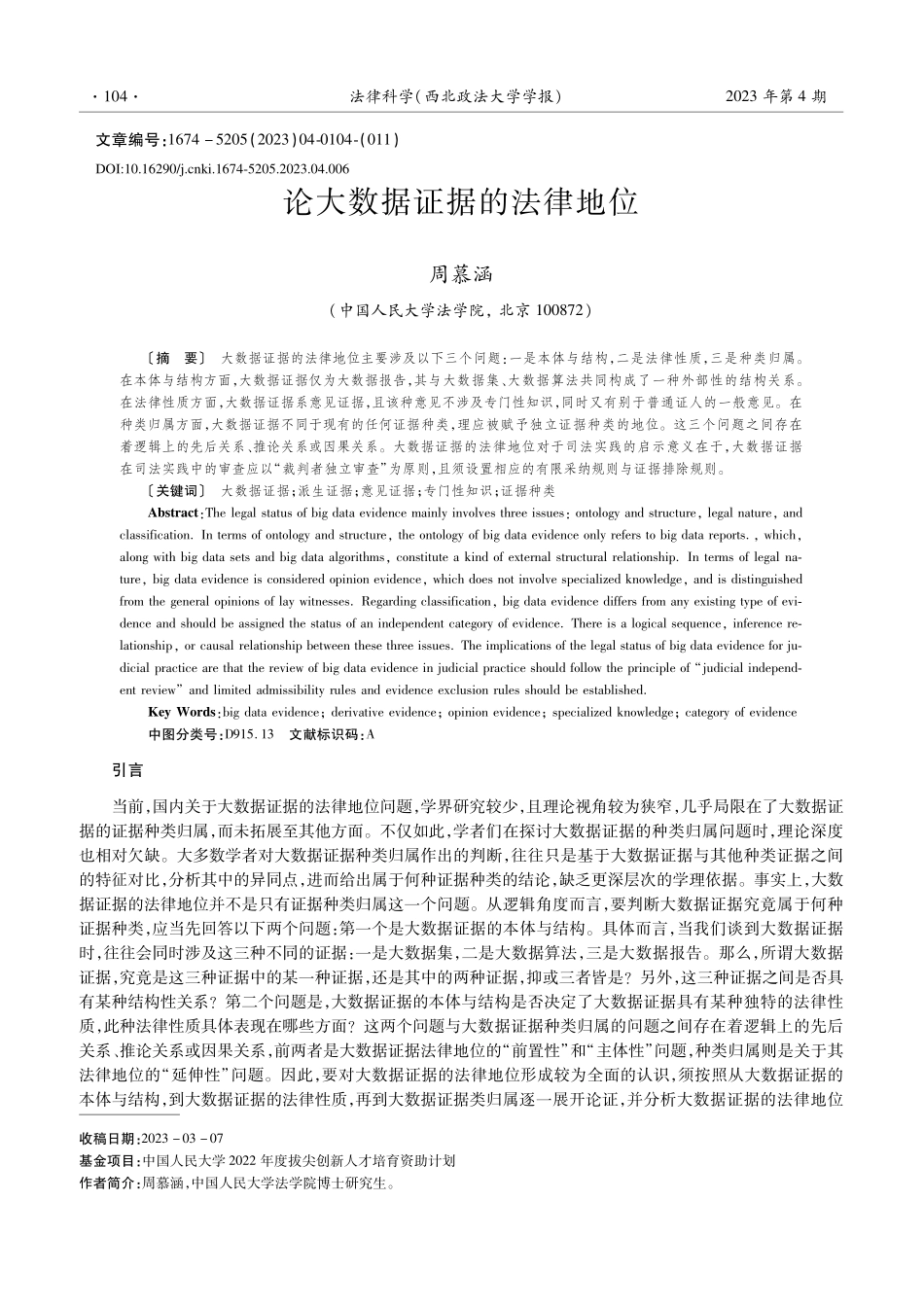文章编号:1674-5205(2023)04-0104-(011)收稿日期:2023-03-07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作者简介:周慕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论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周慕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本体与结构,二是法律性质,三是种类归属。在本体与结构方面,大数据证据仅为大数据报告,其与大数据集、大数据算法共同构成了一种外部性的结构关系。在法律性质方面,大数据证据系意见证据,且该种意见不涉及专门性知识,同时又有别于普通证人的一般意见。在种类归属方面,大数据证据不同于现有的任何证据种类,理应被赋予独立证据种类的地位。这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推论关系或因果关系。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对于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应以“裁判者独立审查”为原则,且须设置相应的有限采纳规则与证据排除规则。〔关键词〕大数据证据;派生证据;意见证据;专门性知识;证据种类Abstract:Thelegalstatusofbigdataevidencemainlyinvolvesthreeissues:ontologyandstructure,legalnature,andclassification.Intermsofontologyandstructure,theontologyofbigdataevidenceonlyreferstobigdatareports.,which,alongwithbigdatasetsandbigdataalgorithms,constituteakindofexternalstructuralrelationship.Intermsoflegalna-ture,bigdataevidenceisconsideredopinionevidence,whichdoesnotinvolvespecializedknowledge,andisdistinguishedfromthegeneralopinionsoflaywitnesses.Regardingclassification,bigdataevidencediffersfromanyexistingtypeofevi-denceandshoul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