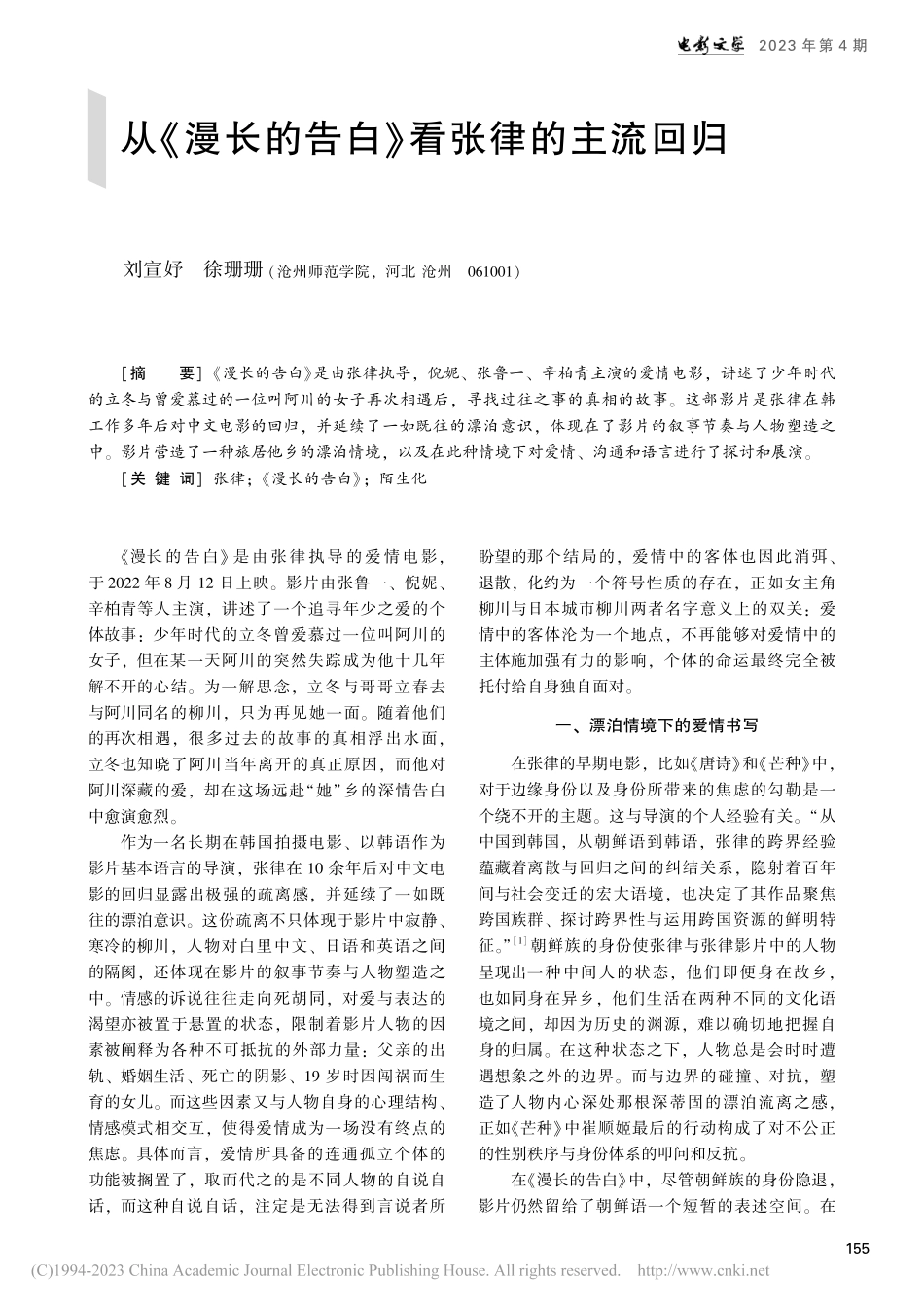2023年第4期从《漫长的告白》看张律的主流回归刘宣妤徐珊珊(沧州师范学院,河北沧州061001)[摘要]《漫长的告白》是由张律执导,倪妮、张鲁一、辛柏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了少年时代的立冬与曾爱慕过的一位叫阿川的女子再次相遇后,寻找过往之事的真相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张律在韩工作多年后对中文电影的回归,并延续了一如既往的漂泊意识,体现在了影片的叙事节奏与人物塑造之中。影片营造了一种旅居他乡的漂泊情境,以及在此种情境下对爱情、沟通和语言进行了探讨和展演。[关键词]张律;《漫长的告白》;陌生化《漫长的告白》是由张律执导的爱情电影,于2022年8月12日上映。影片由张鲁一、倪妮、辛柏青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追寻年少之爱的个体故事:少年时代的立冬曾爱慕过一位叫阿川的女子,但在某一天阿川的突然失踪成为他十几年解不开的心结。为一解思念,立冬与哥哥立春去与阿川同名的柳川,只为再见她一面。随着他们的再次相遇,很多过去的故事的真相浮出水面,立冬也知晓了阿川当年离开的真正原因,而他对阿川深藏的爱,却在这场远赴“她”乡的深情告白中愈演愈烈。作为一名长期在韩国拍摄电影、以韩语作为影片基本语言的导演,张律在10余年后对中文电影的回归显露出极强的疏离感,并延续了一如既往的漂泊意识。这份疏离不只体现于影片中寂静、寒冷的柳川,人物对白里中文、日语和英语之间的隔阂,还体现在影片的叙事节奏与人物塑造之中。情感的诉说往往走向死胡同,对爱与表达的渴望亦被置于悬置的状态,限制着影片人物的因素被阐释为各种不可抵抗的外部力量:父亲的出轨、婚姻生活、死亡的阴影、19岁时因闯祸而生育的女儿。而这些因素又与人物自身的心理结构、情感模式相交互,使得爱情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焦虑。具体而言,爱情所具备的连通孤立个体的功能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人物的自说自话,而这种自说自话,注定是无法得到言说者所盼望的那个结局的,爱情中的客体也因此消弭、退散,化约为一个符号性质的存在,正如女主角柳川与日本城市柳川两者名字意义上的双关:爱情中的客体沦为一个地点,不再能够对爱情中的主体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个体的命运最终完全被托付给自身独自面对。一、漂泊情境下的爱情书写在张律的早期电影,比如《唐诗》和《芒种》中,对于边缘身份以及身份所带来的焦虑的勾勒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这与导演的个人经验有关。“从中国到韩国,从朝鲜语到韩语,张律的跨界经验蕴藏着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