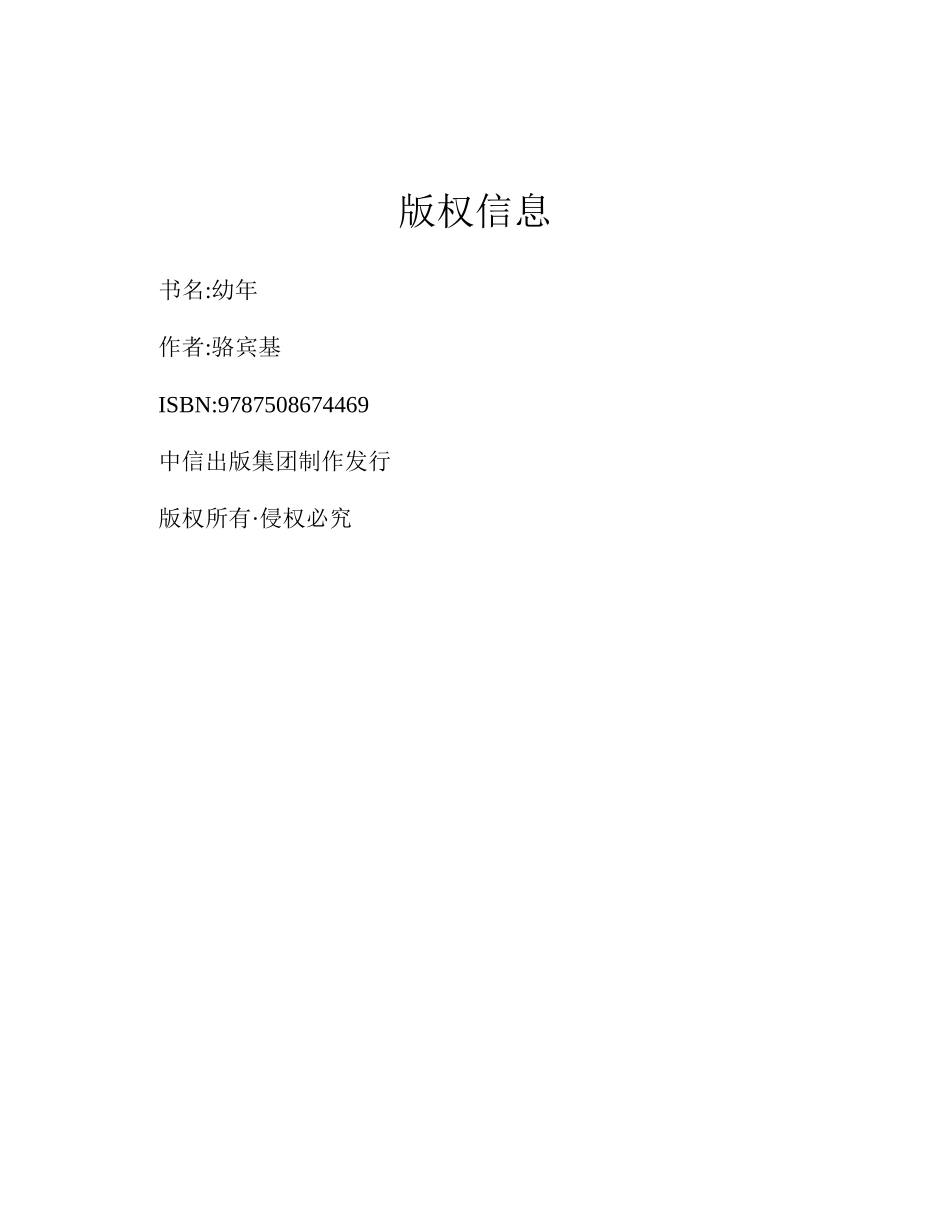版权信息书名:幼年作者:骆宾基ISBN:9787508674469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第一卷第一章红旗河遇险一我出生的县城,靠近海参崴海口的中国边境,距离朝鲜的清津港也很近,所以秋冬两季的早晨,海雾永远都是很浓重的,充满了街道,充满了我们住的院落。每天我一睁开眼睛,就跪在窗口,望着那块现着乳白色烟雾的玻璃,奇怪它为什么在我们吃过饭的时候,会变成透明的,把铺满院子的阳光,窗外的花盆木架和花红叶绿的鲜美色彩都现出来。那时候,我的眼力仿佛还望不到三五尺以外那样远。在我的记忆里,也从来没有一次,从玻璃窗上望见立在对面的一排木窗刻花纹的茅草房子,和那房子前面的摇摆着身子快步走路的鹅,睡在墙角落里晒太阳的猪。除非我跟随着母亲到窗外浇花的时候,若是我走得远一点儿,那些鹅就伸长颈子作势扑我,我这才知道院子里原来还有稀奇古怪的生物。心想走远点看看,可总是给那些长颈鹅围截着,终于两眼望着它们退回来。直到挨近母亲的腿部,我才敢伸脚踢它们。虽然我这样胆怯,可是向来在恐惧它们撕扑的当儿,没有喊过母亲,求援。二县城外,有一条水流清净的红旗河。古远的以往,那些土人聚族而居的年代,北岸或许是给正红旗的满族土人盘踞着的,现在变成了采木行、锯板厂麇集的城郊。河边儿,全是树皮剥光的木排,几乎掩蔽了红旗河的一半水面。有的木排,从这里再顺水下流,运输到图们江去;有的停留在这儿,找到买主,就给搬运到岸上的锯板厂里去,锯作木板。而且一批木排闪出了空位,不久就有另一批木排填补上。夏季的每天下午,城里的妇女们都聚集在这些木排上洗衣裳。僻静的远处,男人站在木排上洗浴,孩子们蹲在木排上垂钓。岸上锯割方木的高架子上,整天不断响着锯木的嗤嗤声、斧锤击打锯板间木塞的叮当声和洗衣妇女们手里不停用棒槌捶打湿衣的捶衣声,还有来往海参崴、清津港的帆船上的水手,遇到一阵把布篷鼓满的有力的风所起的欢叫,所有这些复杂景象和声音,使红旗河在孩子的单纯视感中,成为五光十色的具有诱惑性的乐园了。可是我第一次跟随着母亲到红旗河去,仿佛没有看见宽阔的水流,以及河南岸的绿野、羊群。只是觉得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寻不见那许多声音中最特殊的、古怪的,是发自什么地方,尽是顺声寻望。往往望见的不是发那种奇声的景物,可是这景物本身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到耳里又响起那种古怪鸣叫时,就又抛弃了眼前的景物,去寻望别的了。我所仰望到的锯木架子,是那样高大,如冲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