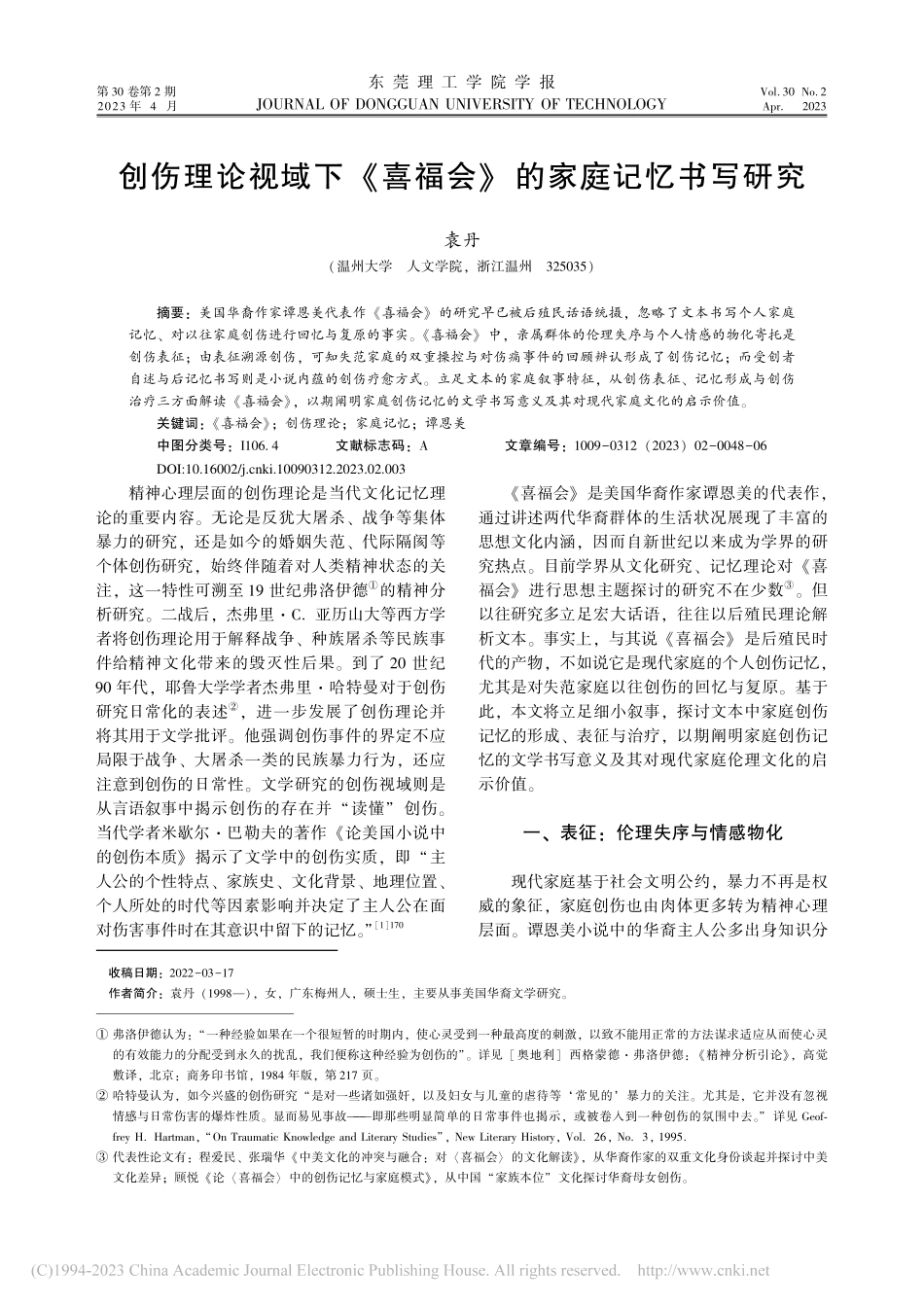第30卷第2期2023年4月东莞理工学院学报JOURNALOFDONGG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Vol.30No.2Apr.2023收稿日期:2022-03-17作者简介:袁丹(1998—),女,广东梅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①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详见[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7页。②哈特曼认为,如今兴盛的创伤研究“是对一些诸如强奸,以及妇女与儿童的虐待等‘常见的’暴力的关注。尤其是,它并没有忽视情感与日常伤害的爆炸性质。显而易见事故———即那些明显简单的日常事件也揭示,或被卷入到一种创伤的氛围中去。”详见Geof⁃freyH.Hartman,“OnTraumaticKnowledgeandLiteraryStudies”,NewLiteraryHistory,Vol.26,No.3,1995.③代表性论文有: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从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谈起并探讨中美文化差异;顾悦《论〈喜福会〉中的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从中国“家族本位”文化探讨华裔母女创伤。创伤理论视域下《喜福会》的家庭记忆书写研究袁丹(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的研究早已被后殖民话语统摄,忽略了文本书写个人家庭记忆、对以往家庭创伤进行回忆与复原的事实。《喜福会》中,亲属群体的伦理失序与个人情感的物化寄托是创伤表征;由表征溯源创伤,可知失范家庭的双重操控与对伤痛事件的回顾辨认形成了创伤记忆;而受创者自述与后记忆书写则是小说内蕴的创伤疗愈方式。立足文本的家庭叙事特征,从创伤表征、记忆形成与创伤治疗三方面解读《喜福会》,以期阐明家庭创伤记忆的文学书写意义及其对现代家庭文化的启示价值。关键词:《喜福会》;创伤理论;家庭记忆;谭恩美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312(2023)02-0048-06精神心理层面的创伤理论是当代文化记忆理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犹大屠杀、战争等集体暴力的研究,还是如今的婚姻失范、代际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