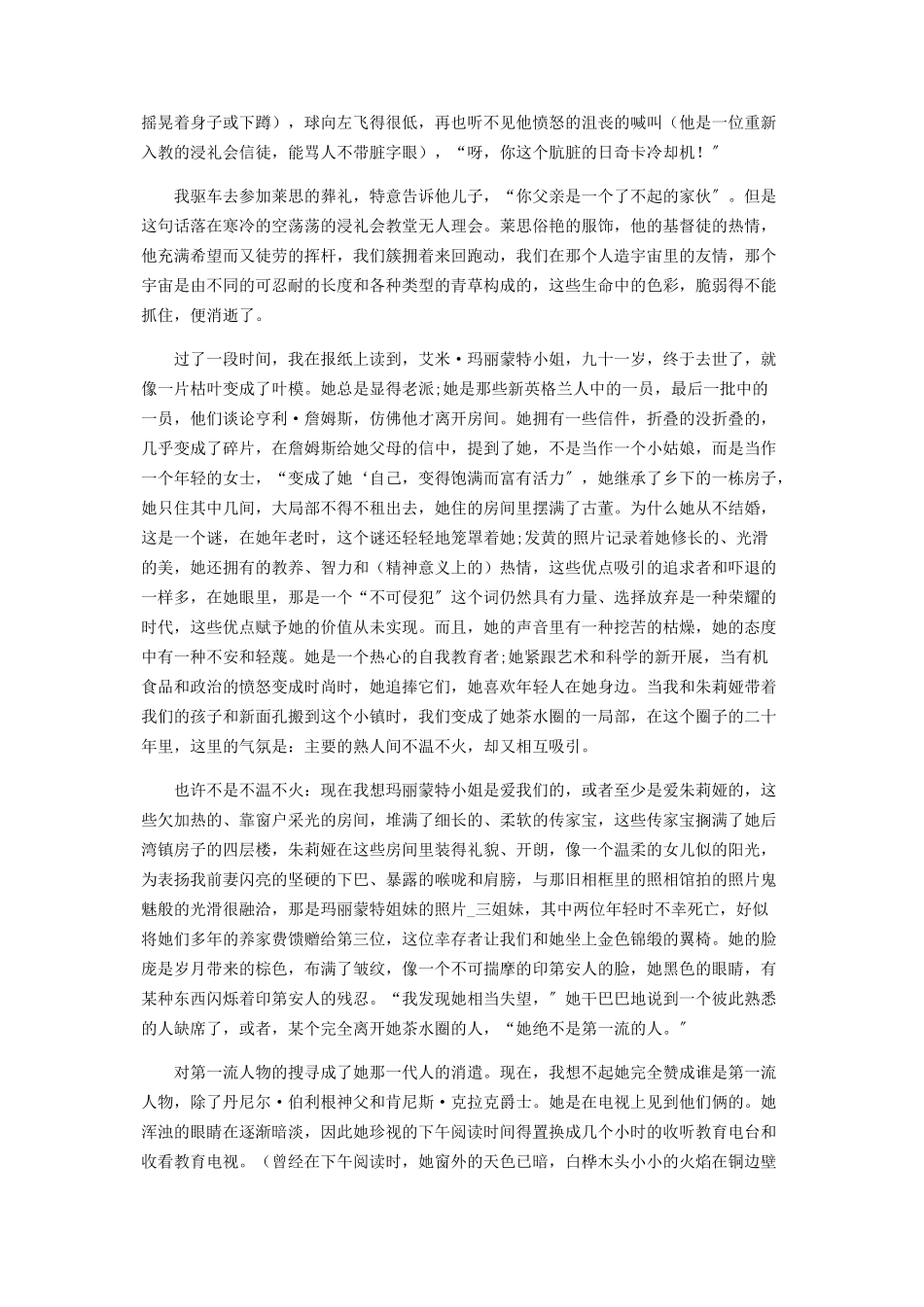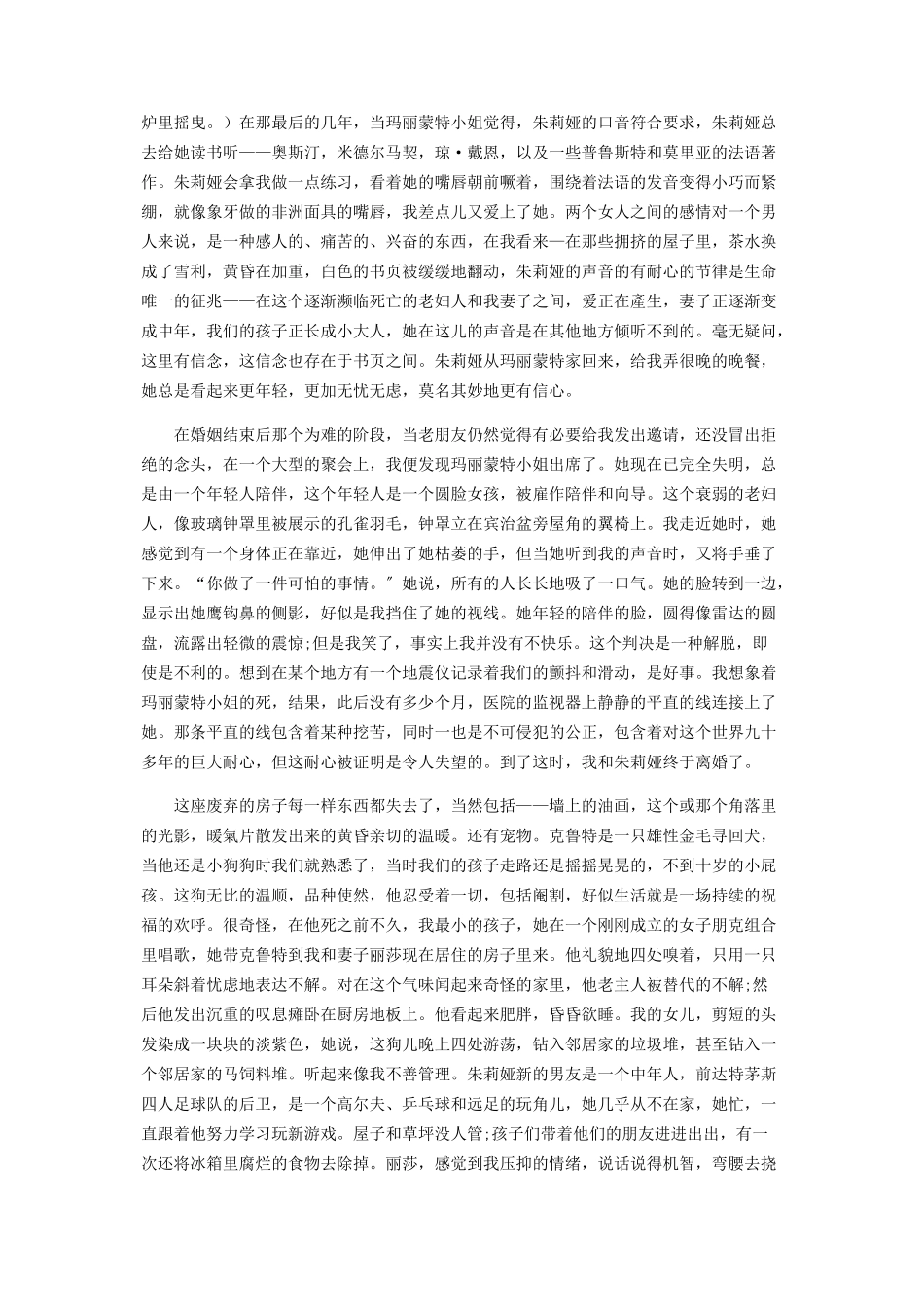远方朋友的死亡[美]约翰·厄普代克著李寂荡译约翰·厄普代克(1932-2023),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小说家、诗人。其一生共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系列小说兔子四部曲贝克三部曲,以及一些短篇小说集、诗集和评论集等),两获普利策奖(兔子富了兔子歇了),两获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厄普代克被誉为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像19世纪的纳撒尼尔·霍桑一样,他是而且将永远是国宝。〞2023年1月27日,厄普代克因肺癌在马萨诸塞州去世,终年77岁。虽然我处于两段婚姻中间已有好几年了,生活于完全被控制的混乱之中,而其他的人继续活着或死去。莱恩,一位打高尔夫球的老伙伴,在医院住了一夜,因为他们说是做一个例行检查,结果倒在厕所里死掉了,他才刚刚给自己的五金店打了个,说他早晨就会回到柜台后面。他是这家店的老板,在阳光灿烂的下午他便让一个伙计打理。他挥杆速度很快,他将自己的重心向后压到右脚上,球经常向左偏出,根本没有飞到空中;但是他在生前还是击出了一些漂亮的推杆,他总是穿戴整洁,似乎预示着对自己的比赛抱有很高的期望。身着金盏花的黄色的休闲裤、天蓝色的高领毛衣、橘红色的羊绒开衫,他驱车从波士顿出发,穿过了痛苦、失眠、道德困惑的云层,在绿色的练习场上挥手。我那么推着小推车穿过沥青停车场,每走一步,我的钉鞋刮擦着,像魔兽的爪子。尽管莱思认识并喜欢我离异的妻子朱莉娅女士,但他从不谈及我的个人情况,或者这样的事实:我从波士顿驱车一个小时来见他,而不是像从前沿着公路开十分钟。在那段时间,高尔夫球场就是天堂;当轮到我走出第一个发球区,我感到自己被封闭于一个透明的宽敞的避难所,平安地与妇女、遭殃的儿童、严肃的律师,以及不友好的旧气氛——整个具有冒犯性的社会秩序隔离。高尔夫有它自己的规那么,它自己的爱,我们三个或四个踉踉跄跄地,朝向每一个球洞,我们一路跟着喊着,嘲笑不好的运气,对少有的相当精彩的击球发出欢呼。有时夏天的天空暗下来,暴雨降临,我们聚集在废弃装备的棚子或者树下,这树相对于它的兄弟们,相对于闪电,似乎不够高,而且脆弱。我们本能的紧张和我们打高尔夫球的兴奋被打断后的不耐烦,在这个棚子的空间里凝聚成热烈的燠热——在啪啪作响的雨声中,喘着气冒着汗的中年男人挤在一块,就像货车车厢里的牛。莱恩的脸上长出许多光化性角化病的斑点;他打算在转化为皮肤癌之前通...